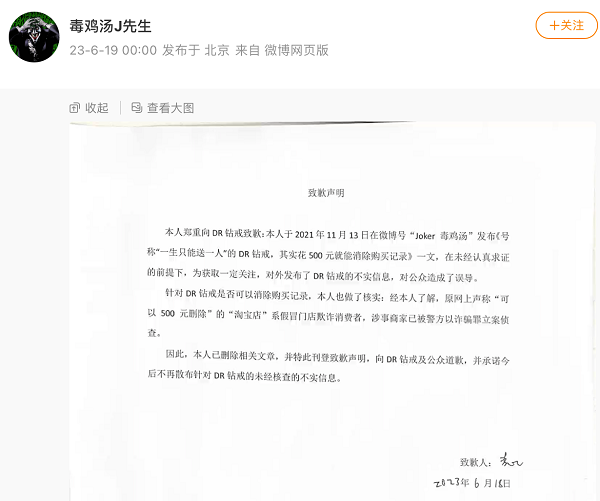你有多久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了?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一家有事,全村吃席。大碗上菜,推杯换盏。
几张饭桌就连成完整的血缘关系网,大事小事,这网都给你兜着:
“都亲人儿,搁谁俩呢。”
而年轻人的生活中,“桌”旁的人越来越少。
最重要的春节也一切从简,率先被划掉的,就是“走亲戚”。
“为什么这届年轻人开始断亲”等词条频频窜上热搜,“断亲”已经成为这届年轻人生活状态的一种注解。
长辈们抱怨:“年轻人怎么如此冷血、自私?”
年轻人回击:“还不是因为你们爹味、多事”。
在Sir看来,两种文化观念的急剧冲突,是社会发展、城市化的必然结果,而“断亲”背后,也有更为漫长和沉痛的心理成因。
断开故乡牵系后,何处才是我们真正认定的“家乡”?
01
消失的亲缘
曾经的乡土中国,亲缘关系决定了你能走多远。
不仅工作由亲戚熟人介绍,亲人还承担了个体的社会保险职能。
△ 《我和我的家乡》中,葛大爷为河北远亲的医保各种操心
物质层面的深度绑定,让“走亲戚”这一人际互动变得举足轻重。
而随着经济高速发展、计划生育的影响,核心家庭迅速崛起,亲缘的物质链条愈发单薄。
城市化不仅带来居住地分隔,更拉开一道阶层差异的鸿沟。
社会关系愈发正式化与科层化,早已不需要亲戚们来获取生存资料。
△ 结果,这位河北亲戚早就上了农村医保
从经济角度看,“走亲戚”早已变成一项“无效社交”。
物质原因外,“断亲”更是年轻人对传统宗法制文化观念的不满,是一种积累已久的“怨气”的体现。
△ 微博上排名靠前的“断亲”原因
亲戚们的第一宗罪,是“没分寸”。
回家过年的饭桌上,最大磨难莫过于各位亲戚的问东问西:
孩子考了多少分?一年能赚几个钱?夫妻吵架是为啥?怎么还是不结婚?
别谈边界和个人隐私,没人想听。
你的答案如何,他们也并不真正关心,要紧的是,自己得根据你的回答作出有面儿的评判。
有了不对,那更好,可以撸袖子开始“表演”了。
别说你嫌弃了,连走神都不成,这可是来自长辈的“指导”和“教育”。
讲到这里,第二宗罪开始显山露水,那就是“虚假”。
剥开宗法等级的外衣,你会看见什么?
答:还是宗法等级的外衣。
刻着长幼尊卑、繁琐礼节的这幢大房子富丽堂皇、精雕细琢,好像啥都不缺。
不。
唯独缺了,人。
年轻人的种种“叛逆”举动的背后,传达着这样的信息:
成为“亲戚”“小辈”的前提是,我是一个值得被尊重、被单独看待的“人”,而不是被一群人打着“亲如一家”的旗号进行攀比和话语权争夺的霸凌目标。
△ 《我的姐姐》中,安然被一群不愿负责的亲戚怒指“不孝”
从某种程度上说,成为“亲人”是最容易的一件事,这是生来就绑定的血缘层级。
成为“长辈”是多么轻易又安全啊,只要钻进这个壳子中去,便天然获得了凌驾于小辈的宗法权力。
但另一方面,成为真正的“亲人”又格外困难。
它要求你突然去接纳另一个体,维系一段并非自由选择的关系。
而那些张牙舞爪的身份扮演总会在某一刻被情感连接的匮乏所击溃,在凄凉中独饮“断亲”的恶果。
△ 《我的姐姐》中,安然真心认定的亲人只有弟弟、姑姑和舅舅,因为他们动了情感,真正“看见”了安然,而非身份强压
02
何处是我新的家
回望背后的故乡,那里有太多被血缘绑架的委屈。
于是我们抛下这些,迈向远方的大城市。
心想,那里,大概会有一个新天地。
断亲之后的社会关系,自然就由朋友来填补。
这是基于三观、志趣的理性考量,是去除了评判与繁文缛节之后主动选择的更加同频共振的“亲人”。
当我们都处于平等和尊重的位置时,爱人的能力也会回到年轻人的躯体。
2006年《武林外传》、2009年《爱情公寓》爆火,大概在于它们打造了一个友情“乌托邦”。
同福客栈中这群人没有真实的血缘关系,雇佣关系也不像现代职场这么森严、苍白。
天南海北,齐聚屋檐下,江湖背后是浓浓的人情味儿。
《爱情公寓》则打造了一个现代都市的童话:
与朋友合租在宽敞干净的大公寓里,暧昧对象敲门可见,楼下约酒每天日常。
然而,剧目是剧目,现实是现实。
都市打工人憧憬着这片“乌托邦”,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准入资格。
有up主查证,爱情公寓的两套房子均超过200平。
换算成上海杨浦区现在的房价,月租大概1w上下。
打工人们卷生卷死之后,付完房租也就不剩什么了。
还有可能遇上这样的局面:
加班到10点回到家,累到一个指头都动不了时,突然想起之前答应了聚会。
强撑着打开手机,发现朋友A忙项目要熬到2点。
而朋友B住在郊区、赶过来要两小时。
你只能放下手机,进入一个短暂的器械保养式睡眠里。
用“友”填“亲”,却发现“卷”没了“友”。
就算拥有了“以友为亲”的乌托邦,那也只能短暂维持。
要么因为工作、城市的变动分居两地,要么一方选择婚恋、分裂成更小的家庭组织。
大城市的背后好似立着一个巨型涡轮,个体如浮尘,行走在极不稳定的事业与情感边缘,稍不留神就被抛出所谓的都市精英叙事,向下漂流而去。
巨大的生存焦虑下,都市青年也无力建立新的亲密关系。
恋爱,比友情还“危险”得多。
当“杜绝恋爱脑,分手保平安”已成为悬挂头顶的十字箴言。
你开始感叹,学生时代对未来的构想太过幼稚。
当时的你,策划着几年后的婚礼是中式还是西式,并把那些情感淡薄的亲戚们划掉,想着只请几桌关系最好的朋友。
结果呢,工作至今,友人不过寥寥,你也干脆打消了结婚的念头。
人不能填补的情感缺口,还有动物、植物,甚至土地本身来填。
△ 电影《租赁猫》
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矛盾景象:
人们靠着《种地吧》和《隐入尘烟》里营造的乡村浪漫图景获得治愈与回归,却急不可耐地脱去真实故乡的缰绳。
人们迷恋原初自然的土地,却无力再去关心这片土地上曾有血脉联系的“人”。
去除了血缘的束缚,为什么还是没能自由?
靠着理性去规划,为什么还是过不好一生?
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?
父辈嘱托年轻人多走亲戚,说他们会成为你的未来保障。
物质与情感双重失效之后,我们不再相信父母口中的那个未来。
但自己想创造的这个未来,又被现实碾成粉末。
断绝的,是亲缘;思念的,是大地;
恐惧的,是他人;丧失的,是故乡。
03
对“故乡”的重新发现
断亲后,最后留在我们体内的情感是什么?
是爱?是恨?还是累?
但很多案例回答了。
最后,其实是“空”。
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在《野草莓》中描绘了一个“三代断亲”的家庭。
主角老教授在冷漠刻板的家庭环境中长大。
母亲只做好场面、不付出任何情感,家庭的交流只有言语讥讽、指责控制。
老教授成家之后也用理性和冷漠应对一切,伤害着自己的周围人。
代际相传的无爱最终集中到教授儿子身上,他用这样一段话拒绝自己孩子的出生:
你为什么会妄图
我们的下一代能创造更好的未来?
我在一个父母无爱的环境中长大
从没有人关心过我
我不愿我的孩子要被带来这样的世界
只要我多承担一天对孩子的责任
我就是多受一天罪
人们都因各自的需要而生活
你的需要是生,是创造生命
而我的需要是死,是永不超生
在老教授即将授封终生成就的那天,儿子这句“永不超生”判决了他真实的人生一一一个无爱又孤独的失败者。
为什么Sir要讲这个发生在50年代瑞典的故事?
因为“彼时彼刻,恰如此时此刻。”
断开所有多余的牵系之后,迎接着我们的究竟是自由,还是空无一切的孤独?
断亲断到最后,断绝的,是我们自己。
失去的,是与这个世界的联系。
不过结局,在老教授坦白他需要情感的现状后。
在梦中,他看到了河对岸的故乡。
野草莓原野上,怡然垂钓、和谐共处的父母亲,在召唤着自己加入。
也有人说,断亲,是“认亲”的冷静期。
是给僵硬压抑的家庭关系按下暂停键,并非永久的断绝和弃置,我们还是会重新踏上“认亲”的和解之途:
或把恩怨放一旁,进行纯粹的理性对话;
或以情感、站在对方角度重新认识,而不是无止尽地抱怨与责任归因……
有些人说,只要年轻人“长大”了、为人父母了,自然就“好”了,就能融入“中国式关系”中了。
Sir想说的是,没有那么轻易。
维系和尊重这门基础课,谁都需要从头学起。
而这种努力也必须是双向的。
毕竟绵延几十年的废墟重建,是一个大工程。
在远离的道路上重新发现自己的“家”,这是比彻底断绝或完全融入要更痛、更难也更了不起的一次成长。
时代裂缝中的这代人,正用一生在名为“父”的巨型纪念碑下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
不要恐惧这“空”,也不要害怕去建立。
另一位电影大师费里尼在自传中讲。
他做过一个梦,梦见他的家是一个大房子,自己是其中一个房间的旅客,而父母是他隔壁的邻居。
这个梦指向他的原生家庭关系:不过是一个寄居的房客。
但他苍白吗?
费里尼仍有电影,仍有数不尽的梦。
更重要的是,他的空房间最终迎来了一个旅伴。
费里尼用影像记录着这段自发建立的、刻骨铭心的关系。
他的镜头对准妻子茱莉艾塔·玛西娜的脸孔——
妓女卡比利亚没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,她穿过马戏团欢乐的人群。
夜那么长,她还是选择笑中带泪地,走在这条大路上。
△ 电影《卡比利亚之夜》最后的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![今日播报![碧蓝档案]第4.5章(完结)条约完结[结尾微桃]](http://img.yazhou.964.cn/2022/0610/20220610102409399.jpg)